穿越汶川|被大地震改变的方向与抉择 重塑山河十年路

2018年1月,外迁的夕格人终于回到故土,戴猴皮帽、穿羊皮褂的释比杨贵生面对洛洛神山,击打羊皮鼓,迎请太阳神去往新家。(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十年前,地动山摇那一刻,家园毁坏,亲人丧生,生计落空。十年间,依靠外力支持与自力更生,这片破碎的土地重获新生,也改变了原本的发展轨迹。
大师手笔再造的美丽城镇、学校,新旧居民如何融合?除了旅游业,发展经济还有什么出路?面对山上的神灵和头上的天灾,羌寨是留还是迁?
2009年初,映秀镇整体重建刚刚启动,中国国家大剧院设计者、法国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给阿坝州政府写了一封信。
他提议,每年或每隔几年,都在漩口中学废墟上覆盖一层泥土,随着时间的推移,芳草和绿树终将掩盖土地的“伤口”。
“对于未来若干代的映秀人民来说,重要的是安静幸福地生活,而不是充当守墓人的角色。”保罗·安德鲁说。他设计的抗震减灾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漩口中学毗邻。
重建时,漩口中学废墟未被抹平,而是刻意地完整保留。它位于映秀镇——5·12汶川特大地震震中。每逢周年,官方的纪念活动多在此举行。

映秀镇,当年的漩口中学遗址整体保留,供游客参观。离遗址一桥之隔,就是广东援建的映秀新镇。(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作为示范样板,映秀镇的重建总体规划由国务院批准,广东东莞对口支援,中外大师参与操刀设计。高规格规划与举国援助,也遍及各个重震区。
十年间,依靠外力支持与自力更生,学校、县城、乡镇、村寨和幸存的人们得以获得重生,而他们脚下的土地,也悄然改变了原本的发展轨迹。
学校:一个母亲的愿望
在毕业生的回忆里,白色校舍围成的“四合院”内,漩口中学的腊梅最香。香消十年,作为遗址的漩口中学,风貌未变,也未被泥土覆盖。残缺的白色楼房孤独矗立,仍是最后的抗争姿势,倾斜、扭曲、断裂、错位、垮塌……
汶川县政协委员王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出于纪念的需要,保罗·安德鲁的建议未被采纳。震后,遗址成了著名景点,旅游业成为映秀百姓收入的重要来源。
而在原漩口中学思想品德课教师陈和琼看来,保留地震遗址还有另一层含义——给幸存者们以警示。
每年临近“5·12”,陈和琼都会来到遗址,一个人绕着废墟行走,和逝去的师生沉默对话。地震中,该校有43名学生、8名教师、2名职工和2名家属遇难。
地震时,陈和琼被塌陷的教师公寓埋了三天,直至被救出。从恐惧中慢慢恢复后,她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如今是七一映秀中学专职心理学课教师。
七一映秀中学,这是漩口中学重生后的新名字。
震后两个月,全国的共产党员交纳了97.3亿元“特殊党费”,其中近20亿元用于帮助灾区中小学校恢复重建。漩口中学获得4600多万元的全额捐建,为表感恩而更名。
副校长徐康志对数字记得清清楚楚:地震前,漩口中学有学生1527名,因为地震导致生源断层,十年后的七一映秀中学,在校生为962人。
新学校按“八级抗震九度设防”标准设计,位于岷江与213国道的夹角处。映秀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多山。人们将岷江上一块高低不平的河滩,用修建都汶高速公路的废渣,回填出一块4.2万平方米的空地。
一切努力,只为寻最安全的校址,建造最坚固的学校。
2009年正月十五晚上,北川县政府举行新县城规划宣传活动。在现场互动环节,第一个上台提问的是一位北川中学遇难学生的母亲。
“她没有提任何个人要求。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规划建设一个安全的城市,把学校建得更牢固一些,不要再让孩子们牺牲了。”北川新县城的总设计师、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至今对此仍然惦念。
全新的映秀小学里,孩子们在上体育课,当年这个地方是运送伤员的直升飞机停机坪。(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重建后的北川中学,是新县城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公共项目,可容纳5200名学生。校内建筑普遍为3至4层,都设有多个紧急通道,学生可在20秒左右逃到室外。
每一年,北川中学都要举行教学楼安全大演练。“不用强调意义,师生都清楚演练的目的。”德育处主任陈钰感觉,演练时大家有一种独特的默契。
幸存的教师,如今只有三十多人仍在北川中学任教,陈钰是其中一位。地震时,他是高三文科2班的班主任。一阵剧烈抖动后,教室直接从三楼掉到一楼,全班学生得以逃生,无人遇难。
这个班级五十多人,有的考上了师范,个别伤残严重的没有参加当年的高考。震后头几年还有联系,最近几年没有聚会,陈钰也说不上来原因,“孩子们现在都工作了,聚不上了吧”。
现在,北川中学每年都要统计,新生中有没有当年遇难学生的弟弟妹妹。陈钰说,对于这批学生,学校不收任何一分钱,老师会给予更多的鼓励和关心。
新生都会去参观校史馆“思源堂”,里面展示着北川中学在各界人士关爱下重建的历史,一块温家宝手书“多难兴邦”的黑板复制品,一块“四川省北川中学”的校名牌匾。
白底黑字的竖匾,是从老北川中学遗址中捡回来的唯一“遗物”。它跟随北川中学师生,从老县城废墟转移到长虹临时校舍,又来到了新北川。
县城:“像个日本城市”
“新北川到了,你在哪里下车?”大巴从北川老县城所在的曲山镇出发,由北往南穿过擂鼓镇、永安镇,终点在永昌镇——北川新县城。
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县城是北川。大地的强力穿城而过,老城区80%的房屋倒塌,同年9月又遭受洪水泥石流的袭击。
英国立博官方网站无法就地重建,县境内亦无适合建城之地,距老县城曲山镇23公里,隔壁安县境内的一块地被划入北川,命名为“永昌镇”。北川成为5·12地震后唯一整体异地重建的县城。
2011年2月2日,北川举行了一场以“开启永昌之城,点燃幸福之火”为主题的盛大开城仪式。时隔7年,对于这座严格遵循设计师规划建成的县城,人们依然称呼它“新北川”。
大巴车一一报出街道名字,先下车的是“老北川人”,住新县城北部的尔玛小区和禹龙小区;后下车的是原安县农民,住偏南部的新川小区和永昌小区。
初次到来的游客,可以居中选择,在羌族特色步行街下车,站在这座县城的中轴线上。环顾四周,建筑低矮错落,行人不多,仿佛置身于一座规整的大型新开发楼盘。
北川新县城的中轴线,富有“羌调”。新北川拒绝高楼,远处的羌碉是全城制高点。(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在细节上像个日本城市。”李晓江不止一次从国际同行那里听到这样的评价。他喜欢这个评价,“北川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高层住宅的县城,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理想,老百姓也很接受。”
2018年3月,李晓江回访新北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新县城的设计者们要编一本书,检验当年的城市规划设计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李晓江被安排住在2016年开业的佳星酒店,这是新县城里第二高的建筑,16层。“(佳星酒店)不是住宅,(建得高)也就算了。”规划新北川时,李晓江建议,这里的建筑无论如何不要超过12层,兼顾安全和美观。
最高建筑是羌族碉楼,位于步行街中心,高37.7米,周围建筑只及它的腰部。碉楼门口循环播放着一段女声录音,热情邀请“各位朋友乘观光电梯,到北川最高的羌碉上观看北川灾后重建的成果”。
步行街两侧,却有大片空地。在新县城规划设计征求民意时,设计者们原本认为,居民们会优先考虑县城里这个最繁华的地段,结果相反。
老安县人要往南住,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在南边;老北川人要往北住,他们希望离失去的家园越近越好。于是,这两侧的用地只能留作备用。
“我们尊重了他们的选择,但这确实是个遗憾。”李晓江说,虽然新建的小区都不设围墙,但一南一北的地理区隔,阻碍了老北川人和老安县人的融合。
今年回访,李晓江专门询问当地居民融合得怎么样。他看到,在永昌小学里,即便是地震后出生的孩子,有时也会分成两拨玩耍。
在李晓江看来,社群的融合,还需要时间,加强基层社会组织的建设。
乡镇:想了很多办法
重建之初,除了传统的旅游业,北川也寄望于工业能拉动经济。
在新县城东南角,对口援建方建了一座产业园,引进新材料、机械设备制造等企业,“工业不景气加上根植性不好,很多很快破产了。”李晓江说。反而是食品加工厂、啤酒厂等本地企业,在园区里发展得红火。
李晓江2015年曾带领团队做过调查,产业园区里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工厂能开工。原来希望产业园区能吸引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实际只提供了两三千个就业岗位。
汶川县南部寿溪河畔的水磨古镇,一门心思搞旅游。这里原本倚重重工业,地震后,政府将铁合金厂、电子厂等63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迁出。
“2013年是最好的时候。”原本在铝厂打工的程磊,这一年起改开出租车。古镇处处羌族风情,由广东佛山援建。“这里一切都是新的,活下来的人好像到了一个漂亮的新地方,重新活一遍。”
2010年,全球人居论坛授予水磨镇“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之后两三年,全国各地的游客自驾、组团前来观光,热闹的时候,“从水磨到都江堰的路上塞满了车”。
这几年,虽然游客少了,好在2011年搬来阿坝师专(现为阿坝师院),有八千多在校生,又带来了人气。
昔日工业重镇汉旺,地震前以东方汽轮机厂为绝对的经济支柱。80后青年吕伟回忆,在他小时候,汉旺就像一座移民城市,天南地北的人们在这里因为东汽落脚、扎根,自给自足。
昔日工业重镇汉旺在东汽搬离后,需要寻找新的出路,由于一些学校也搬离,孩子们在汉旺只能念到初中毕业。(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东汽厂区工业遗址门外,汉旺广场钟楼的时间永远停在14时28分。十年前的那一刻起,“十里东汽”在汉旺的时代也终结了。
“说起来挺唏嘘的,和东汽在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吕伟说,损伤惨重的东汽在地震后泪别汉旺,迁往德阳经济开发区。一同离去的有两万职工和家属。
原地异址重建的汉旺新镇,距离地震工业遗址向南不到3公里。新镇面积扩大了一倍,居住人口却只有原来的一半。路上难见年轻人。吕伟住到了绵竹市区,偶尔回来看望曾在东汽工作的父母。以前在汉旺做生意的舅舅,也搬到了德阳。
东汽中学和东汽技校也搬走了,汉旺的孩子读到初中毕业,就要去往他乡。“以前对东汽依赖度太大,东汽走了,现在完全找不着北。”吕伟说。汉旺的重建在2011年基本结束,当地政府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发展康养产业。但他感觉,这座城镇至今还没回过神来。
吕伟把希望寄托于尚未全线通车的绵茂公路。这条公路全长56公里,建成后将缩短成都与九寨沟的距离,但因施工难度大,通车时间一年推一年。他盼望,等绵茂公路通车了,区位优势提升的汉旺也许能重建产业、重现繁荣。
村寨:贴纸条监测山险
时隔十年,汶川县龙溪乡大山深处,阿尔村村民再次住进避险帐篷,面临和十年前一样的艰难抉择:迁徙,还是留守?
2018年4月8日晚,阿尔村发生了山体滑坡,原本植被茂盛的大山留下一道褐色“伤口”。泥石倾泻而下,淹没了部分房屋。
2018年4月8日晚,阿尔村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淹没了部分房屋。时隔十年,村民再次面临去留抉择。(南方周末记者谭畅/图)
“这次可能真的要永久撤离了。”几天后,村民余永清回到家中住了一夜。房子是震后新建的,2017年刚还完贷款,真要告别,他心里恋恋不舍。但留守意味着危险,夜深人静时,从房子里还听得到山上传来的窸窣落石声。
余永清的房子建在群山谷底的巴夺寨,是阿尔村四个村寨中海拔最低、最安全的村寨。十年前,当时的阿尔村村支书就在巴夺寨的空地上宣布了一个让人沮丧的决定——全村撤离。
震后,地质专家将阿尔村勘测为“已不适合人类居住”,警告滑坡和泥石流随时可能将这里掩埋。这个云端上的羌族村落一度举村迁移,在他乡避险一个月。然后,又回来了。
“这是一段失而复得的生活。”老释比马永清曾这样说。在羌族社会,释比是“神的使者”,通晓天地。因为不愿离开祖祖辈辈耕耘的羌寨,马永清是当年率先回到阿尔村的“八勇士”之一。
阿尔村在原地重建家园。国家有资助,公益组织有援助,再加上免息贷款,村民们按照抗震强度7级以上的要求建起了楼房。新房保留了羌族特色,内部是钢筋水泥结构以抗震,外墙仍以石片垒砌。新房窗户四角绘有羊角图腾,古羌人奉羊为守护神,寓意家宅平安吉祥。
这十年,阿尔村人时刻不忘地质专家的警告。环绕阿尔村的“神山”有几处裂缝,村民们用土办法监测:在裂缝上贴纸条、塞木屑,如果纸条断裂、木屑落下,说明裂缝在扩大,危险可能降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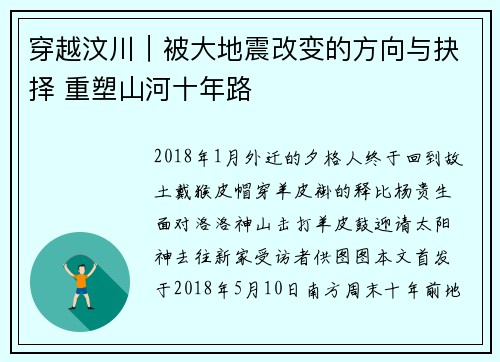
4月8日下午3点,今年担任监测员的巴夺寨组长朱光跃例行查看,发现一处裂缝不但纸条断裂,还有小石头从上方落下。
他打电话通知村主任,下午5点全村紧急撤离。两小时后发生山体滑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山上有一座羌碉,在当年地震中已损毁成了危房,本要拆除,村民们与文物局商议后保留了下来。这次山体滑坡,马永清眼见着它一层一层垮塌,顺着泥石滑落山下。前一天似有预感,他从碉里抢救出14面羊皮鼓。羌人祭祀时,释比要击打羊皮鼓歌舞,与“神灵”对话。
地震后,余永清担忧,羌族文化渐渐无人传承。释比文化是羌族文化的核心,余永清开始学习做释比,拜龙溪乡夕格村的老释比为师。
夕格村在地震后只剩废墟。2009年5月,全村人按照政府整村重建统一搬迁计划,迁徙到240公里外的四川邛崃市南宝山安家。出发前,夕格人要和世代受其护佑的山神、水神、羊神、神树林,以及深睡在山野之中的前辈先人一一道别。
人迁徙走了,神还留在原地。村里的释比杨贵生主持了一场祭祀,允诺三年后将神接到新家,继续护佑夕格人。
三年过去,夕格人自觉还没适应新地方,还没安顿好新生活。直到2018年1月,他们终于回到夕格。太阳落山时,戴猴皮帽、穿羊皮褂的释比杨贵生面对夕格人尊敬的洛洛神山站立,击打羊皮鼓,迎请太阳神。他用音调悠远的羌语吟唱:“请跟我们走啊,请跟我们走!”
纪念园:“这是想事儿的地方”
从喧嚣的映秀镇向西而去,群山深处,牛圈沟自两山间蜿蜒而下。冷清、蛮荒、鲜有人至,时间仿佛停滞。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巨大的爆炸声首先从这条山沟内响起,紧接着沟旁的山体像波浪一样连绵垮塌。专家称,相当于有251颗原子弹在牛圈沟爆炸。
蔡家杠村村民王俊每次放羊从旁边的小路经过,都会习惯性地望向这条山沟。那里长眠着他的爷爷奶奶——他们可能是地震69227名遇难者、17923名失踪者中,离震源点最近的人。
地震那天上午,17岁的王俊还看见爷爷在屋外休息,如今碎石早已掩埋了曾经的小屋。王俊还会去石头上坐一坐,抽根烟:“不全是因为想他们,只是觉得那个地方有一些熟悉的味道。”
震后,王俊家曾在山沟处垒起一座空坟,石碑上只刻着名字——王汉章、张术华。这座简单的空坟,成为王俊祭拜爷爷奶奶的地方,也成为寻访者进入震源的标志。
2010年,泥石流又将空坟淹没。此后王俊家未再垒空坟。
渔子溪村向阳的缓坡,曾是映秀镇西侧最好的耕地。地震遇难者公墓建在了这里。
2008年5月,映秀镇上大量的遇难者遗体必须找地方掩埋,人们选中了这片向阳的缓坡,挖了三道4米深、3米宽、150米长的大坑和许多零散的小坑。
古稀之年的胡建国是这里最早的守护人。坑都封上后,胡建国每天打扫台阶两个小时,归拢并焚烧散落四处的纸钱,一一点燃熄灭的蜡烛,这样的工作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
胡建国守护数千亡灵度过了震后最初的时光,其中包括他11岁的孙子胡正军。和大多数遇难者家属一样,胡建国不知道孙子埋葬的具体位置,只知道就在这山坡上。
后来,坡上正式建起了盘旋而上的三层公墓。
在北川老县城,原本建商住楼的一个地基基坑,在震后掩埋了无法及时外运的遇难者遗体,并建成公墓。一片绿草松柏环绕,一块没有镌刻人名的石碑只有三行红色数字:2008.5.12、14:28。
和漩口中学一样,整座北川老县城也被刻意地完整保留,作为“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2018年5月,媒体刊发的新近照片中,一所学校宿舍楼上仍拴着当年逃生用的床单。
23公里外的北川新县城,中轴线上建有一座抗震纪念园,分为静思园、英雄园、幸福园三片区域。静思园是一片银杏树阵环绕的幽闭空间,下沉步行路径穿过一汪静止水面,水面形如泪滴。设计者最初设定的主题是祭奠,和幸存者们交谈,了解他们的心理诉求和生死观后,改为思考人生之地,让劫后余生的人们与上天和亲人对话。
北川老县城作为遗址,已向公众开放,最近每天都有不少人前来参观,并向遇难者纪念碑献花。(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2010年10月,李晓江参加完欢送对口援建队伍的大会后,来到静思园。一群刚参加完欢送的北川中学学生也走进园子。李晓江问学生,这里是什么场所。一位学生回答:“这是想事儿的地方。”李晓江无比欣慰,重生的北川人理解了他们要开启新生活的这片土地。
英雄园还有一个更受欢迎的名字——新生广场。2018年4月一个平常的傍晚,新北川的孩子们在广场上学骑自行车、溜旱冰、奔跑嬉戏。广场边的河道里,一蓬蓬萱草恣意生长。萱草叶脉修长,花开鹅黄,在春风中摇曳,别名“忘忧草”。

立博官方网站广州豹队是一家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足球俱乐部,原名广州影豹足球俱乐部,注册成立于2023年3月23日,主场设在黄埔体育中心体育场,主要参加中国足球乙级联赛。广州豹队在2025赛季中甲联赛中表现出色,新...